不少人或许知道白先勇先生是一个勇敢的同性恋作家,1976年,他写了有同志恋情题材的小说《孽子》,这也是华文文学同性恋书写的开山之作,是划时代的作品。
但关于白先勇的恋情,更能表达他自己的是那篇感动千人万人的“以血泪、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”——《树犹如此》。
这篇散文,是为纪念他的同性恋人、生死之交王国祥而作。白先勇说,他和王国祥的感情里,“包括朋友、爱人、儿时默契的伙伴等多重含义。”
下文节选自《树犹如此》。在书的附录中,面对访谈,白先勇还讲述了自己关于同性恋的一些看法。
▲ 《树犹如此》节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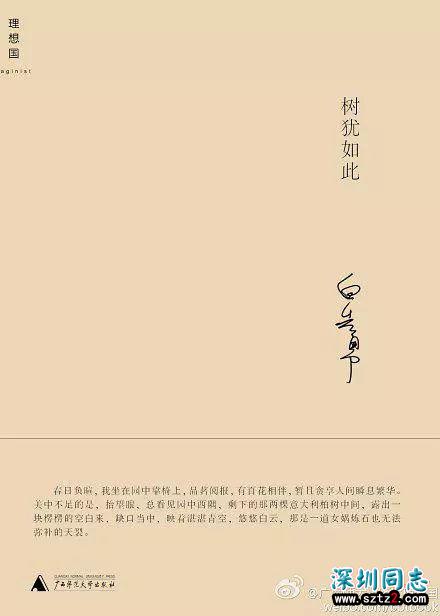
理想国丛书《树犹如此》
白先勇|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十年树木,我园中的花木,欣欣向荣,逐渐成形。那期间,王国祥已数度转换工作,他去过加拿大,又转德州。他的博士后研究并不顺遂,理论物理是门高深学问,出路狭窄,美国学生视为畏途,念的人少,教职也相对有限,那几年美国大学预算紧缩,一职难求,只有几家名校的物理系才有理论物理的职位,很难挤进去,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曾经有意聘请王国祥,但他却拒绝了。
当年国祥在台大选择理论物理,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、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鼓励。后来他进伯克利,曾跟随名师,当时伯克利物理系竟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教授。名校名师,王国祥对自己的研究当然也就期许甚高。当他发觉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无法达成重大突破,不可能做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,他就断然放弃物理,转行到高科技去了。当然,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实现,这一直是他的一个隐痛。后来他在洛杉矶休斯(Hughes)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,研究人造卫星。波斯湾战争,美国军队用的人造卫星就是休斯制造的。
那几年王国祥有假期常常来圣芭芭拉小住,他一到我家,头一件事便要到园中去察看我们当年种植的那些花木。他隔一阵子来,看到后院那三株意大利柏树,就不禁惊叹:“哇,又长高了好多!”柏树每年升高十几呎,几年间,便标到了顶,成为六七十呎的巍峨大树。三棵中又以中间那棵最为茁壮,要高出两侧一大截,成了一个山字形。山谷中,湿度高,柏树出落得苍翠欲滴,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,金碧辉煌,很是醒目。三四月间,园中的茶花全部绽放,树上缀满了白天鹅,粉茶花更是娇艳光鲜,我的花园终于春意盎然起来。
一九八九年,岁属蛇年,那是个凶年,那年夏天……有一天,我突然发觉后院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那一株,叶尖露出点点焦黄来。起先我以为暑天干热,植物不耐旱,没料到才是几天工夫,一棵六七十呎的大树,如遭天火雷殛,骤然间通体枯焦而亡。那些针叶,一触便纷纷断落,如此孤标傲世风华正茂的长青树,数日之间竟至完全坏死。奇怪的是,两侧的柏树却好端端的依旧青苍无恙,只是中间赫然竖起槁木一柱,实在令人触目惊心,我只好叫人来把枯树砍掉拖走。从此,我后院的西侧,便出现了一道缺口。柏树无故枯亡,使我郁郁不乐了好些时日,心中总感到不祥,似乎有什么奇祸即将降临一般。没有多久,王国祥便生病了。

白先勇与中学时代至友王国祥合影
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
(访谈者:PLAYBOY杂志,以下简称P)
P:你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?
白:我想那是天生的。
P:在外国,尤其是在英国,中学、大学的学生之间的同性恋现象相当普遍。在台湾和香港,由于社会和道德的压力,这种事至少在表面上不常发生……
白:那也不见得。台湾的中学,因为男女分校的缘故,同学之间有亲密感情的也不见得会太少,尽管这种感情是过渡性的。你可以问问台湾的男孩子,他们在中学时期,大都有形影不离、分不开的好朋友,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很暧昧,也许是不自觉的。香港的情况不一样。说到香港,我倒要问,香港到现在(同性恋)还是违法的吗?
P:还是不合法的。
白:就是嘛,有了法律的规定,就不一样了。台湾没有那样的明文规定。
P:不过,香港的青少年未必都知道有那么一条法律,他们只是有一种犯罪感……
白:但犯罪感还是因为法律而生的,法律上规定不许那样做……
P:在大陆,许多男孩子牵着手在街上走……
白:对,满街都是。
P:外国人见了一定会以为他们是同性恋的,但在中国,那却是很自然的事。
白:我觉得那是一种珍贵的感情。人与人之间,发诸自然的感情都是可爱的,自觉地去扼杀这些感情倒是污辱人性。

白先勇
P:你刚才说,中学生之间近乎相爱的感情往往是过渡性的。事实上,无论过渡是自然而然,抑或是自觉的压抑,绝大部分人到了一个阶段就会改变。
白:绝大部分都是如此的。对同性的爱慕是青少年时期的感情,大部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,就会把感情改放在异性的身上,当然也有人继续下去。改变的原因复杂不一:对异性的渴求、对家庭的向往,又或者由于社会的约束和压力。美国的情况很有意思,一方面很开放,许多州都取消了反同性恋的法条,但在另一方面,美国社会对这问题的态度虽然比较香港宽容得多,但也要看哪个圈子。文艺界、文化界基本上是相当宽容的,所谓straight society的“端正”人士,却仍旧相当忌讳这个事情。
我觉得人很奇怪,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?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一样呢?人生下来,本来就各有不同嘛,即使是异性恋,每对恋人的爱情都不一样。我觉得凡人都需要爱,无论是怎样的人,而且除了在感情的领域之外,同性恋者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P:同性恋跟对异性的畏惧有没有关系呢?《寂寞的十七岁》里的杨云峰害怕女孩子,你自己年轻时是否也有过这种心理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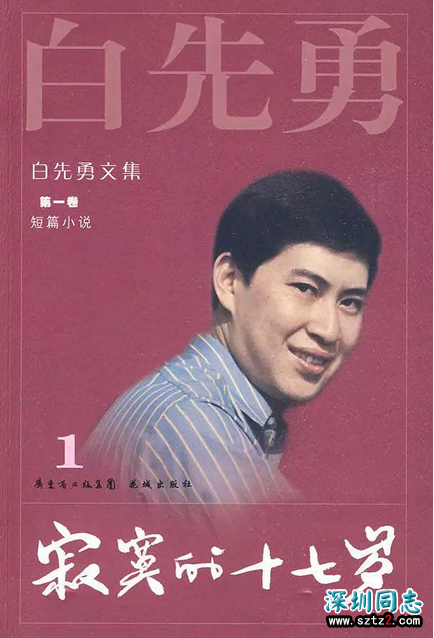
《寂寞的十七岁》
白先勇| 著
花城出版社
白:我想一般年轻的男孩子对异性都有或多或少的惧畏。成熟之后,这种心理就会消失。不光如此,我觉得同性恋不但不怕异性,而且往往能够与异性结成好朋友,建立很积极的友情,也许那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吧?当然,肉体的结合是一种很宝贵的经验,但有时候,不论是同性还是异性之间,超肉体的、精神上的结合是可能的,而且也是很可贵的。美国诗人Allen Ginsberg(艾伦·金斯堡,“垮掉的一代”代表人物之一)与他的男朋友……
P:Peter Orlovsky。
白:对,Peter Orlovsky。他们第一次见面时,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。Ginsberg后来在回忆里称那次交谈是soul exchanging,灵魂交换,好像在这世上找到另一个自己。我对同性恋是这样看:异性恋所找的是一个异己、一个异体、一个other,同性恋呢,找寻的往往是自体、自己、self,在别人的身上找到自己。这是同、异性恋一个基本的不同。
P:男女相爱而结婚或同居,生孩子,好歹是一辈子的事,一对同性恋人却似乎很难保持一生一世的关系。
白:那是一定的,因为异性的结合有家庭的鼓励、社会的保障、法律的约束、对儿女的牵挂等等因素把两人锁在一起。感情因素当然很重要,但夫妇关系的维系并不单只凭感情。相反地,一对同性恋人在一起生活,可以依赖的却只有互相的感情,而人的感情是多变的、脆弱的,往往禁不起考验,再加上外界的压力,就更难长期地维持下去。因此,同性恋人要长久在一起,必须克服加倍、加倍的困难。不过,在同性恋人中也有白头到老、终身厮守的动人故事。我写过一篇谈《红楼梦》的文章,文中所论很能代表我个人对同性恋的看法,题目是《贾宝玉的俗缘》,希望你有机会找来看一看。

《白先勇细说红楼梦》
白先勇| 著
理想国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我觉得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、非常神秘的东西,古往今来,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真的百分之百了解人性。人性中有许多可能性,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一样,一百对男女有一百段不同的爱情故事。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规定一夫一妻、结婚年龄等等,人的感情却不可能因此而理性化、制度化。同性恋,同性之间所产生的爱情也许也是人性的一部分。
同性恋不是一个“突变”,而是一种超文化、超种族、超宗教、超阶级、超任何人为界限、自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的现象。其实我也不懂得其所以然,只知道它的存在。世俗的法律规定只是为了方便于管理一群人,这些规定往往能够适合大部分人,但不一定适合其余的那一小部分。法律如是,社会的习俗也一样。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异性恋——金赛报告说,人类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异性恋——因此也难怪全世界都以异性恋为正常,世界各国的法律都以异性恋为标准。然而,从来没有一套法律、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灭人性中同性恋这个部分。
对于同性恋,像对人性中其他的因素一样,我们应该深入地去了解,了解也许可以助长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容忍。同性恋者也有权去表达他们人性上的需求,因为他们也跟任何人一样,都需要爱情、友谊和沟通。我的看法是这样。我并不同意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中某些人的言论,他们走到另一个极端,认为同性恋者高人一等。我并不认为有特别抬高同性恋的必要。其实,大家都是人,平等的人,最要紧的是互相了解,了解之后就会产生容忍。
P:虽说人人平等,但在实际的社会里,人却并不平等。在世人——社会上的大多数——的眼里,同性恋始终是一种异端邪行。你小说中的人物,就往往处于“边缘人”的位置。
白:我就是觉得marginal man最有意思。我最不会写中产阶级、“典型”夫妇的生活,可能我不擅于描写“大多数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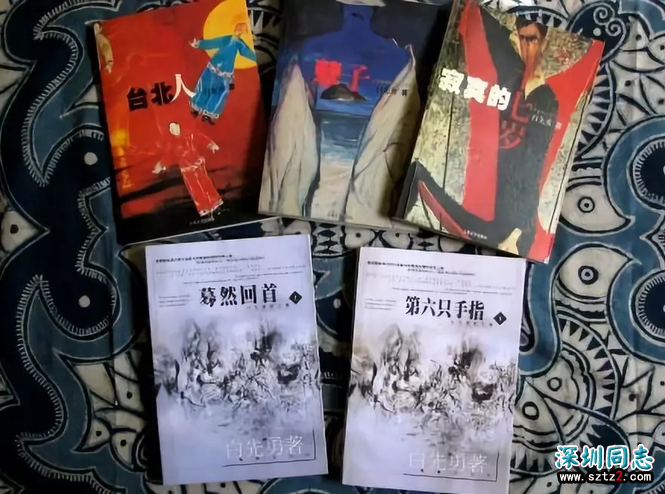
白先勇书籍封面
P:在西方著名的文学家、艺术家之中,同性恋多得不可胜数,有人甚至认为同性恋是艺术家和作家的“理想人生”!
白:其实那也有点道理。同性恋一向是社会上的少数派,社会的道德习俗都不是为他们而设的,有时甚至是反对他们的。因此,他们不从俗,对事物有独特的看法。那的确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材料。艺术家不能自囿于成例、俗见,必须有独往独来的感性。处于“边缘”的个人以及民族,如犹太人、爱尔兰人等,有大成就的着实不少。这同时也因为他们受到中心社会的排斥,经常要提高警惕,注意四周,因而对人和事物往往都比较敏感。
P:但被排斥、受压力,长期处于社会“边缘”的处境是不好受的吧?你从来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,随俗而安?
白:我当然体会到、感受到外界的压力。不过我想我自小便是一个蛮能保持自我的人,即是说,我不会因外界而改变自己,也不会有任何外来的压力足以改变我。
PLAYBOY中文版,一九八八年七月号
同性恋这个事情我一向不认为是种羞耻
(访谈者:刘俊,以下简称刘)
刘:您在谈到《玉卿嫂》改编成电影的时候,您说主要是反映一个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死亡和爱情问题。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,认同危机是个比较大的问题,您本人有没有这个问题?

《玉卿嫂》剧照
白:有,绝对有。
刘:有,那么具体内涵是……
白:很多方面。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的背景,这个跟我的历史观的变化很有关系。一九四九年以前,我在大陆的童年世界,虽然已经有很多波动,因为我童年经过抗日,但那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世界,在我个人来说,家境那时候也好,可以说是我爸爸得势的时候,在中国那时已经是蛮高层的家庭,我们其实是不自觉地过着那种贵族的生活。后来一下子,四九年以后到台湾去,我父亲的政治地位跟整个社会、整个国民党,突然间的一种转换。那时候我当然不是那么懂,可是我想对我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。这对我认同感方面的问题影响很大。
第二,在文化方面,现在回头想想,我父亲他们那个时候,以他的那个年纪,我们家里,并不是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那种东西。其实我妈妈也很反封建,也是一个革命分子。她奶奶要裹她的脚,她大反抗,她那时才七八岁,脚痛得“哇哇”大哭,跑去踢她奶奶的门,后来放掉了。她跟我爸爸结了婚以后回广西去念师范,还参加过学生游行。我爸爸那时候参加辛亥革命,在他那个时代他们是第一代往前走的人。我出生在那么一个家庭,慢慢也很受儒家的思想熏陶,但我们生为第二代,往前更跑得快了。
刚刚说同传统冲突,其实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文化危机一个一个接连不断,除了历史、政治以外,我们回头看看,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大崩溃的时期,而我们就卷入其中。后来我们从桂林到重庆,然后到上海,住在上海。在中国来讲,上海是西方文化的窗口,洋派。在这种环境下,我对西洋文化,已经有些沐染。然后在香港,又是一个洋化的地方。到台湾后又念西洋文学,所以西方文化对我的冲击必然造成认同上的各种各样的适应问题。那时也不懂,现在回头想想那时一定很复杂的。所以我想文化上的认同也有各种的冲突。
第三,我个人的成长。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——我在很小就开始朦朦胧胧地感觉到,在这种情形下,就觉得与人不同。
刘:大概什么时候?
白:我大概很早,童年时候就觉得与人不同。我在很早就意识到这种,背负了一种认同上的……
刘:那时候您父母不知道?
白:他们不知道,我自己朦朦胧胧的,觉得这种个人感情好像与人不同。这样子以后,尤其在我青少年那个阶段,我就变得很孤立。这个identity,这种认同,对我也很重要,对我整个的文学创作,很重要。因为同性恋者的认同必然地觉得自己是受了社会的排斥,他们是少数人,他们的道德观也不接受世俗的道德,他们有很独立的看法,很多很多文学家、艺术家,都跟这个有关。这个跟我的独立思考很有关系,我青少年时代的认同危机,也同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。
刘:您是在什么时候在心理上很坦然地对待这个问题的?
白:很坦然告诉别人的时候?
刘:不一定是告诉别人,就是您自己心理上没有负担了,您自己已经释放自己了,认为自己在道德上……
白:我一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种羞耻。
刘:很小的时候?
白:一向不认为。而且在我来讲,可能我比较奇怪一点,我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,还觉得是一种骄傲,有不随俗、跟别人的命运不一样的感觉。我想我跟很多人不同,有些人有同性恋的问题,因为社会压力,觉得有些难以启口,抬不起头来。但同性恋对我来说,造成我很大的叛逆性,这个是满重要的一点。
一九九〇年九月于上海静安宾馆
 深圳同志网
深圳同志网

